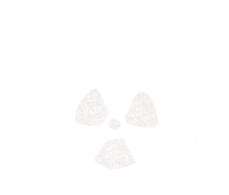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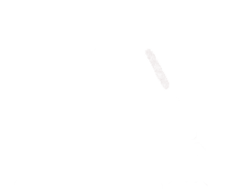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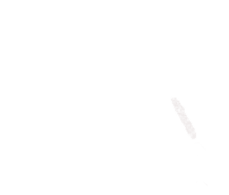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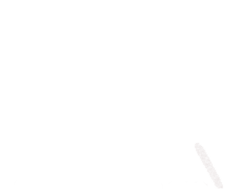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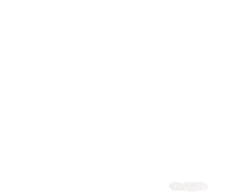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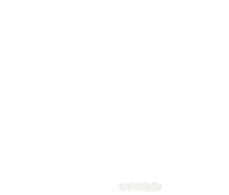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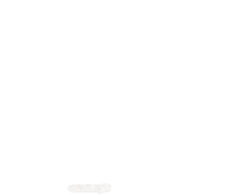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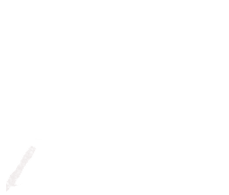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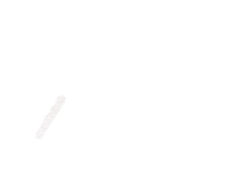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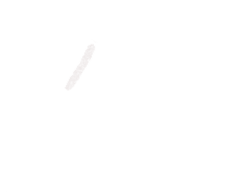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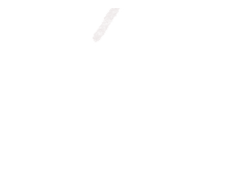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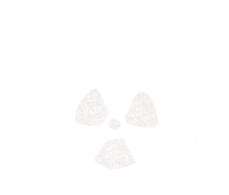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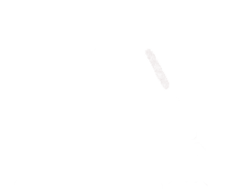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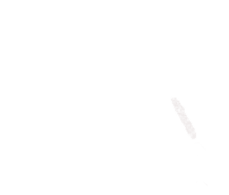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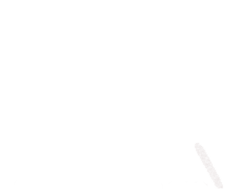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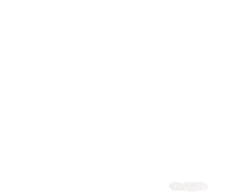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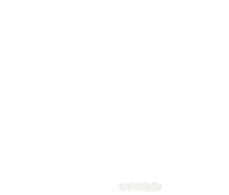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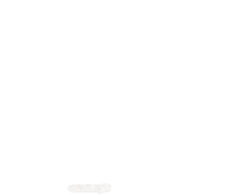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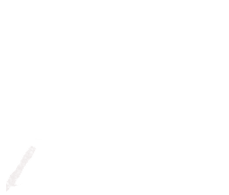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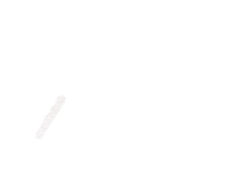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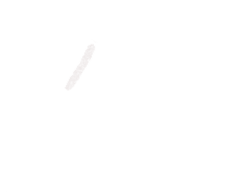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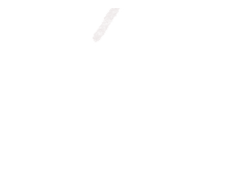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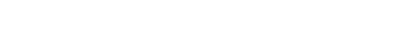

輪胎持續輾軋樹枝,沾滿泥濘。鮮紅的警告標語再度出現。若再往前一步,就等於自擔罰金900萬白俄羅斯盧布(約630美元、18990新台幣)的風險。
只有在每年復活節後9天,核災禁區會敞開2天大門,允入緬懷。核電廠被一片「紅色森林」圍繞,那些死於放射線的松樹群,仍聳立於人們口中的薑棕色墳場。往外,出現塌陷水泥路、廢棄學校、破舊屋舍,河面飄著擱淺的船隻。
1986年,35萬居民在不明所以的倉皇中,被蘇聯政府以夏令營、馬戲團等藉口強制遷村。建築物被迫割捨或剷平、房屋地基遭覆土掩埋。
但這一切,阻擋不了對家園極度的想念。卅年來,陸續有老居民翻回禁區,千方百計,在空蕩的森林裡覓地而居。
無人的森林廢墟一隅,偶爾鑽出野兔身影。
窗邊一只碗,盛滿發霉白飯。


29年前,這裡本有人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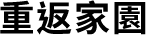
即使死寂桌上擺著一碗發霉白飯,屋裡仍飄滿活躍的灰塵,如同每一棟散落朽木床板、菇菌、藥罐、針筒、破門的屋舍,以及格局簡單可辨的傾頹食堂、校舍、教堂。
29年前的屋主或許倉促離去,匆匆撕走相簿幾張照片、散落一地鞋襪。也或者翻箱倒櫃的痕跡,肇因於核災事故後的竊賊,其對掛在牆角1986年4月起無人撕去的日曆、78轉黑膠唱片、蘇聯時代政宣報章興趣缺缺。
窗外竄出野兔、山貓,隨即溜走。一台腳踏車載著老男人的身影晃過。我們發動引擎,緊跟其後,見男人消失於某處上坡路段前,敲過一扇民宅的門。
叩、叩。木門嘎滋打開。應門者是75歲的凱特,男人的母親。她堅持留我們作客。戴著耳環的凱特修剪一頭整齊而服貼的短髮,穿鮮豔亮色家居洋裝,像在這空寂卅年的小鎮,殷殷期盼著訪客隨時出現。
縱使頭、手基於不明原因在我們面前抖個不停、無法抑止,凱特引我們到菜園,驕傲似地介紹100平方公尺以上的綠油油菜田──胡蘿蔔、青蔥、高麗菜……,幾乎望不到邊。照顧菜園時,她身子仍來回抖動,吃力卻嚴謹的動作看得出意志堅強。
不一會兒,她竟已將炒馬鈴薯、青蔥奶沙拉、醃漬番茄、炸黃瓜等佳餚送上餐桌,來回交換位置,怕擺盤不美。
「這些食物很安全,多吃點,吃光光!」她邀請。晚飯很美味,我們讚不絕口。凱特的臉上終於露出難得而欣慰的笑容:「大家都羨慕我的菜園。」
「大家?」我們懷疑附近還有人居。
停頓了一會,凱特囁嚅。其實,以前的鄰居都不見了,回來的都是超過80歲的老人,也一個一個死了。
「有個冬天,我和朋友回家。穿越菜園時,衝出一群狼,咬住我的腰。我痛得大叫,終於嚇跑牠們。但朋友整張臉被咬爛,死了。」戈梅爾(Gomel)和侯尼齊(Hoiniki)的醫生檢查過凱特身體狀況,皆無大礙。但她因揮不去那次驚懼,從此以後,頭和手總不停抽動。「我再也不敢轉頭,我好怕!」
她領我們到客廳看電視,如同每日作息。牆上滿佈著玩偶與照片,她解釋:「那是我的凱莎妮雅,她很聰明、很聰明。」孫女出生在車諾比核爆的1986年,好不容易長大、準備上小學,卻突然被驗出原因不明的腦部病變。
孫女最後死了。凱特黯然,丈夫已撒手人寰,現在除了一塊搬回災區的大兒子,其他兒女也都遠了。
「我好怕一個人孤伶伶地死掉……」堅持住在老家、卻害怕就要這麼孤單一輩子的她,壓抑著雙唇,頭和手卻依舊來回擺動,無法抑止。


每當風從烏克蘭吹來,意外地,儀器上的輻射數值瞬間飆高3倍。季節風,加上卅年前蘇聯策動的人工雨,使白俄羅斯被迫犧牲、接收高達70%的車諾比輻射塵。
輻射災區外圍一些,一張長凳上坐著7個老奶奶,曬太陽,緊握著購物袋。
小貨車抵達,司機跳下駕駛座、打開後車廂:「這是我私人車」,他很驕傲地告訴我們:「每周來2次,檸檬水最受歡迎!妳得去阿沙瑞維奇(Asarevicy),很漂亮的地方。」奶奶們在各種果汁、香腸、麵包、番茄醬、零食、衣褲間挑選。有時來的是政府車,商品種類少,但會載來居民盼望的信件和包裹。
85歲的瑪麗亞,已經很久沒有接觸外頭世界。她沒聽說過,近10年政府正策劃第一座興建於白俄羅斯的核電廠。
憶起車諾比那天,她突然激動地掩住雙眼,喊著:「大災難,大災難!」「二戰時,我親眼看著人殺人,縮在暗處的我被烏克蘭人救起。可是車諾比……比戰爭更恐怖!」她雙手合十、閉眼搖頭,恍若歷歷在目:「我在農場看見黑雲,以為快下雨。可是天空變成一種詭異的橘色,愈來愈亮、愈來愈亮,」她顫抖著雙手:「回到家,老公說核電廠出問題了。」
她沏茶不斷,把剛買的火腿、麵包、起司都擺上桌,難為情地說:「對不起,招待不周。我們以前那棟老房子比這裡舒服,我好想回去,但它不在了。過陣子,我會搬到較好的屋子裡。」
櫥櫃充滿藥罐,瑪麗亞說自己光胃部就有三個手術,得不斷和體內輻射搏鬥,但政府的藥物津貼已取消多年。
櫥櫃內牆貼著丈夫年輕的照片,「他很英俊,」我們的翻譯員附和。一張相似的面孔進屋,是他們53歲的兒子,在附近的生態保護區擔任司機,也看過同一片橘色天空。
問瑪麗亞,丈夫上哪兒了?「去世了。」她眼神茫然,只是望向窗外。兒子補充:「爸爸罹癌。」
我們沒再提起那座新的核電廠。
窗簾飄動,瑪麗亞靜靜地坐在餐桌前。
核災當天,瑪麗亞丈夫透露核電廠爆炸的消息。
他隨後死於癌症。
瑪麗亞一邊哭,一邊不斷勸我們飲食。
鏡內是他剛回家的兒子。
沙維奇(Savicy)一間雜貨店,某位老人聽見「車諾比」,驚呼,恐懼般地不斷重複那3字。「我們人類,一直在破壞地球上的和平與友誼,」他抽抽搭搭哭了起來:「村裡這些人都沒有機會過好日子。」
二戰後,他才能夠回到這兒,靠在墓碑上,和被德軍射殺的弟弟說說話。沒過幾十年,又面臨車諾比。
這些老居民被迫遷離,卻忍不住想念家園、搬回來繭居。他們面對自己的下一代,則一面惋惜兒女遠去、一面堅持推離兒女。
正如芙拉。她很清楚輻射不會在瞬間殺死人,而是在之後慢慢地殺。一個和煦美麗的午後,她踩上一張木桌,摘取樹上櫻桃,舉手指向不遠處的普里匹特(Pripyat)河,說小孩曾熱愛在那兒抓魚。「其實那樣不安全,我5個小孩身體都有問題。」如今,兒女搬到明斯克(Minsk,白俄首都),一年回來一次。
「那裡比較適合居住,而且政府規劃復元假期,提供小朋友療程。幸運的話,每年還有機會到歐洲呼吸3個禮拜新鮮空氣。」
不過,近年政府已取消這種復元假期,也不再提供碘片等藥品。64歲的她比劃著自己心臟、骨頭:「這裡、這裡……老是出現問題。」核災後,許多事都變了:「很多鄰居好端端的,突然就死了。」
她打開大門,邀請我們進入菜園。50平方公尺的土壤種滿櫻桃、馬鈴薯、杏桃、包心菜、小黃瓜、南瓜、蒜頭、甜菜、洋蔥、胡蘿蔔、草莓、紅椒、蘋果、番茄。她一心盼望將兒女拉拔長大,今日終於有3個孫子,健健康康。
這些菜圃,如同蘇聯政府允許白俄居民擁有的一間達剎(dacha,遠離塵囂的小木屋),讓每個家庭至少還能擁有最後一塊豐饒的避風港,遑論農產品安全與否。
芙拉尚不敢掉以輕心:「小孫子們年紀還小,即使患有隱疾,也不一定能看出徵兆。像我小孩們的身體,潛伏到青春期才出現毛病。」
芙拉無法斷定孫子們的身體是否都健康。
菜園裡自種的櫻桃。
得踩上一張桌子,才能站得夠高,足以搆到櫻桃。
塔緹安娜的災區老家,距離高濃度輻射區不到100公尺。但政府表示,此地居民無法享有醫療津貼。
年輕時是幼稚園老師的她,時常忘情地唱起歌來。然而每當憶及車諾比,瞬間痛苦皺眉,哽咽地用雙手摀住眼、耳,來回撫動:「那天我剛好要和爸媽團聚,從烏克蘭回來。看見消防、救護、警車連夜奔馳,進出村莊,但沒有人告訴我們怎麼了。」
「媽媽看著我的兒子被強推上貨車,整晚一直哭:『為何他們要搶走我的小孫子,噢,噢,天啊。』」
「我不該抽菸的,我不該,」她放下剛點燃的菸,邊說邊流淚。「政府要把爸爸載走,說去洗身體。他躲在豬圈好多天。」母親先去世,父親苦撐著罹癌的身子,依舊在3年前宣告不治。
她講到一半,突然恍神:「女孩,不要把妳的鼻子鑽得太深。你們知道太多,會很危險的。」她翻箱倒櫃,遞來一份報紙,提起多年前因追蹤弊案被暗殺的記者表哥。
塔緹安娜走出屋外:「那裡有座山,埋著我們所有人的雞蛋。政府說,蛋很危險,給我們酒,說可抵抗輻射線。一人一瓶,小朋友也要喝,日日夜夜,持續5年。就是這東西殺了白俄人!」
「我老了,沒力照顧那麼多蔬果,有些只能任它亂長了。」
塔緹安娜看著自己的菜園。
通常,大門是深鎖的。
電話鈴響,朋友打來慰問
塔緹安娜說自己不該抽菸,卻還是忍不住一口又一口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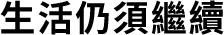
附近的樹林和空屋住著許多羅姆人,被謔稱「吉普賽」、「茨岡」。某次遇見兩個披頭散髮的老女人、一個面容憔悴的老男人,跌跌撞撞鑽進後座。整台車瀰漫濃烈的伏特加氣味。他們不斷親吻我們雙手、搓揉我們頭髮,驚呼:「好久沒看見外人。」
這群人來自莫斯科北方,住進車諾比災區內廢棄房舍,擔任雇工,採集蘑菇──吸收最多輻射物質的蔬果之一。
偶爾,路邊有些形影單隻的好心人會提醒我們折返,別被政府發現。
永遠無法預料鑽往愈深處,會遇見什麼樣的小小社會。
某次大雨傾盆的午後,60歲的建築工人搭上我們便車。齜牙咧嘴、帶著渾身酒味的他,說話不急不徐,平靜地引我們到一座120年歷史的教堂。
他曾駛著巴士,親眼目睹車諾比核災那團黑雲。當時政府強制遷離家人,但17年後,父母太思念故鄉,他便陪著他們搬回老家。
經過這12年,父母也過世了。剩下他還在這,日夜修築教堂:「2周後,我也要退休了。」這座教堂保存極為古老的祈雨儀式,因而即使村內只有20個居民,每周末,仍有信徒自四面八方湧來。
教堂旁,仍有老婦在雨中牧羊,相較之下我們躲入木造涼亭的身影顯得不夠瀟灑。「這幾年總雨量變少了,降雨卻變得集中且暴烈。」遠方,迷濛中漸漸展開一道彩虹。「那不是彩虹」,他說:「你們看,7種顏色的雲聚在一起。」
只要不提起往事,災區內的生活與災區外沒有太多不同。人們仍過著生活。
若不仔細看,這就像一條尋常的路,
有騎著單車的人、有閒晃的狗。
森林深處,出現一座教堂。
男人陪父母搬回核災區老家。
父母死後,自己也即將在此終老。
穿越空曠玉米田,眼前矗立一座不知收集何方廢棄物的垃圾場。回頭雜草叢生,但不乏色彩斑斕的野花與巴掌大的蒲公英。許多舊時房屋只剩地樁,地基被水泥與覆土填上。
樹林偶見豎起的人造建物,小小一尊,飄著刺繡白布,被荒煙蔓草包圍。附近全無建物,詭異的卻是有些墓碑上的卒日在車諾比後──看來,許多人堅持回到老家度日了。復活節左右,每逢災區開放2天,親人方能重返墳墓旁野餐,紀念難得的聚首。
一些回到災區的老居民表示,核災並未改變什麼。也不擔心新的核電廠。
卡納塔普(Kanatop)一對硬朗的老夫妻,日夜照顧花團錦簇的前院:「離開的人都死了、或是不健康,但妳看我們,多麼強壯!」他們說,政府曾於車諾比隔年限制食用肉、魚、蘑菇等,但很快就解禁。「我們村本有人輻射值2.11,後來降到0.11;也有人被測出22,大家都以為他活不過明年,幸虧後來降至0.15,而且現在95歲了,活跳跳的咧!」令人驚訝的數據記憶。
我沒有問,是不是常有人問起他同樣問題。
再往南,原有400多戶人家、今日卻空蕩的一個村莊,零星遷回幾戶養育貓、狗、雞、鴨的家庭,溫暖好客,不斷將覆盆莓送給我們。問他們是否擔心新的核電廠。一戶說:「政府有說,大家需要電。」一戶說:「呃,都這麼老了,無所謂了。」
不斷地探索核災區直到國界的盡頭、在其中穿梭並居住數日後,我們折返,朝向首都的方向。
回到明斯克,一間樂聲悠揚的餐館內,彼得想念著回不去的兒時老家,念念不忘那個陽光燦爛的周六,24歲的他汗水淋漓、歡樂地和朋友踢著足球。無人知曉車諾比已爆炸。頃刻,政府強制居民在一天內撤離,母親只得獨力攜家中5口輾轉遷徙。第一個寒冬,他們靠零星家具與6200蘇聯盧布(計算通膨後約今日1.5萬美金、45萬元新台幣)撐過。16年後,母親死於胃癌。
「車諾比毀了很多家庭。直到現在,我都還常常夢見綠蔭環繞的老家,那裡有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。」彼得說:「現在,房子都壞了,我只能在每年復活節後帶著鮮花回去看看,再到父親的墓旁坐一兩個小時。」
戈梅爾有名男子,也是每逢假日,就回到雙親在都柏史(Dobrush)的老宅。雖然父母都已過世,前一棟房舍也因核災而遭剷除,他表示:「我依舊喜歡回這裡打掃。至少還有個安靜地可以看星星、呼吸新鮮空氣,逃離城市。」
核災禁區內,有些墓碑來自1986後的亡者,遷回家鄉長眠。
居民送給我們許多剛收成的覆盆莓。
久久未見外人的居民拿著一桶覆盆莓,與我們道別。
「那裏有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,」
遷居至首都明斯克的彼得,深深想念著老家。
回憶中的家園早已不存在,無論被掩埋、或遭拆卸。假若1986年的這些居民是蘇聯軍人,便可能站在災區邊緣,眼睜睜看著司機偷偷載走一卡車自己滿是輻射的老家碎片、遭肢解的房屋建材,看著它們被送往災區外、送往全世界,築成別人的新屋。
「妳要記住我們的故事……」塔緹安娜說,「離開白俄後,很久很久以後。」